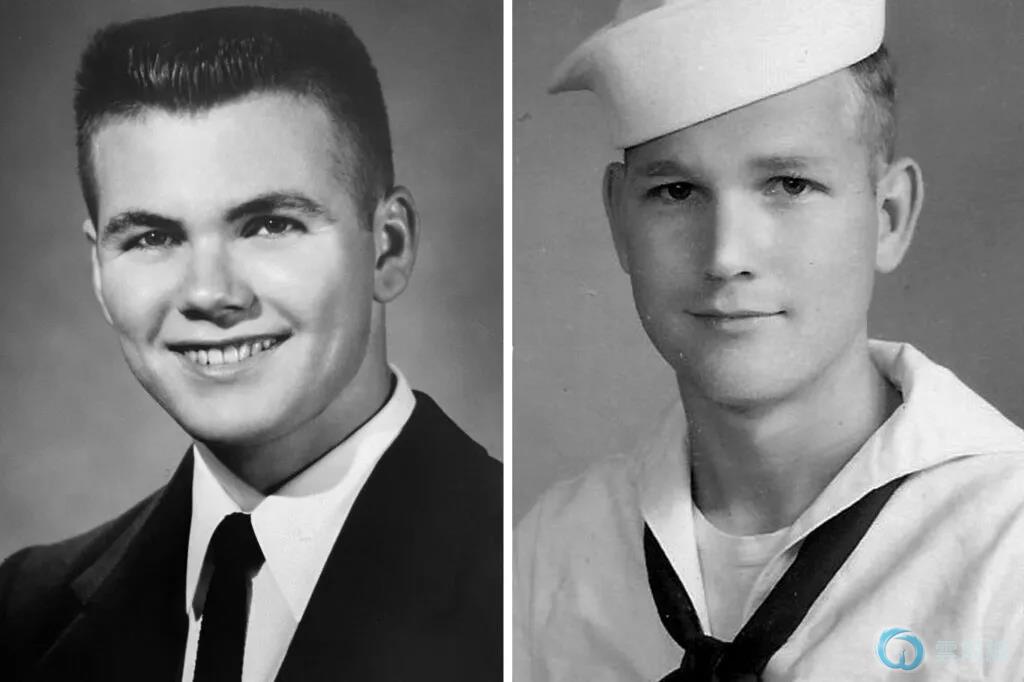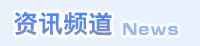 |
|
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十年影响力人物公共卫生之张北川:被边缘化的坚持者
在一个对同性恋仍存偏见的国度,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学者本身也要遭遇歧视和偏见。他多年以来坚持不懈,呼吁正视同性恋和艾滋病感染者,并把一个被社会完全边缘化了的人群当成自己的朋友,他创办的《朋友》就是他和同性恋人群沟通的紧密途径。
他被人称为“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”;他与卫生部副部长一道,被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授予艾滋病防治特别奖项;而他自己却说,“我就是一个医生。”
为了从事同性恋研究,他不仅放弃了自己擅长的皮肤科专业,而且被医院领导无端剥夺了行医资格,被迫栖身于一间没有取暖设备的半地下室开展工作。“每个人都有自由恋爱和结婚的权利,不论同性之间还是异性之间,只有爱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要为这些边缘人争取空间。”
张北川的经历被媒体曝光后,这个充满书生气的知识分子被冠以“斗士”“最有勇气的人”之名。
但从事了近20年同性恋研究的他,却始终在质疑自己的工作,“有些东西,我是悲观的,这辈子我可能都看不见了。但我来了,做了,就对得起医生的良心”。
“他们是正常人”
张北川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,进入同性恋研究领域的。
那是在1989年。当时,他还是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一名大夫。“我的一位老师,被揭发出是同性恋,受到恣意侮辱和伤害,逼得他想跳楼,站在楼顶上号啕大哭。”这件事给了张北川很大的震动。“他是一位很优秀的皮肤性病科医生,富有献身精神。有一次,为了研究一种皮肤病,刻意让自己染病。然后,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,切下自己被感染的皮肤做实验。”
但对于老师的遭遇,他却无能为力。张北川发现,自己对同性恋几乎是一无所知。于是,他开始研究同性当中相互爱慕的现象。
“那时,我常常要学习到凌晨两三点钟。医院和医学院两个图书馆的300多种医学期刊,我一期一期地翻,找相关的文章。”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,他每次去图书馆借的书总是非常多,以至于不得不用两个大菜篮子,把它们提回来。
在研究的过程中,张北川又开始了写作。为了抓紧时间,他还在自己办公室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字条:一般谈话不得超过15分钟。
5年后,张北川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同性恋的理论学术著作《同性爱》。
“我习惯用‘同性爱’,而不是‘同性恋’。同性恋这个词已被污名化,我希望鼓励和支持一种富有情感的性关系。”
在这本书中,张北川指出,同性恋的形成与先天因素和婴幼儿时期的成长环境有关,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社会都有2%~5%的人是同性恋者,“他们同你我一样,也是正常人”。
《同性爱》出版后,张北川本打算回去继续从事皮肤科研究,但他发现,自己已经放不下了。“我接到无数封充满了彷徨、无奈、绝望的求助信和求助电话。这些遭遇让我感到自己肩负的是一个沉甸甸的社会课题。”
一位同性恋者在信中写道:“像我们这种人,一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打上了不幸的印记,注定了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灰暗的。我努力过,追寻过,但最终找不到路,找到的竟然只有离开世界这一条路。”
张北川意识到,自己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个的个体,而是一个人群,以及隐藏在他们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。
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