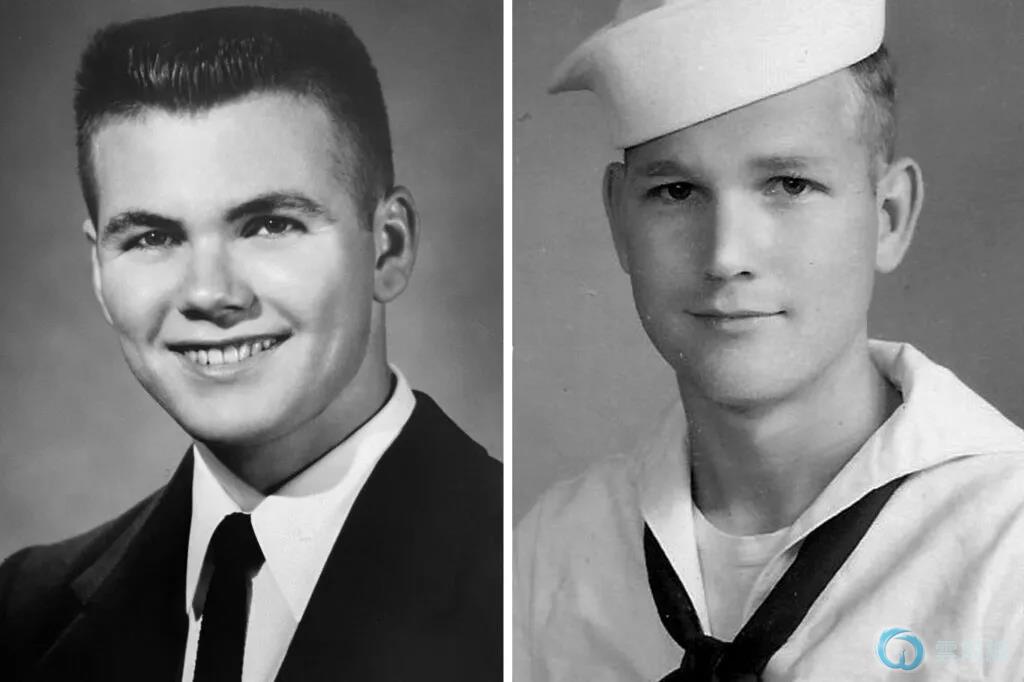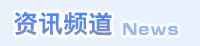 |
|

一个警察带着一个同性恋来医院,问:这到底是流氓还是精神有病?有病就留在医院,没病我就带走。
世卫组织早就宣布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,但中国医学界对此仍长期存在分歧,留下盈利的空子和尾巴,同性恋求医者成为“送上门的肉鸡”。
中国同性恋者的“平权运动”远比想象中困难。一个民间自发开展的调查报告发布会,邀请的精神医学家没有一个到场。
吴振躺在沙发上,看见咨询师捧着电击仪走了进来。他看了看,有点像高中物理课上的毫安表,上面写着“厌恶疗法治疗仪”。
咨询师让他躺好,全身放松,闭上眼,想象同性的嘴和身体,想象和他们亲热。
吴振想象不出来,那个方头方脑的机器,像一对怪眼,让他紧张。
不过五六分钟,咨询师将电极刺向他的手臂,虽然只是一下,但电流冰冷,他还是一骨碌跳了起来。
这是一次价值五百元的体验,事后,吴振得到一张收据,抬头写着“同性恋矫正”。
这更像是一次卧底,身为“同志”,吴振反对成为矫正的对象,但这之前,他并不知道这样的矫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,直到电流过体,他想,这种痛苦,真的没必要。
2014年3月,吴振将重庆心雨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告上了法院,同时成为被告的,还有百度公司,只要在其网页搜索“同性恋矫正”,置顶的总是这家机构。
这只是冰山一角,2013年,同性恋公益组织“北京同志中心”曾向全国十个省的十家同性恋矫正机构寄去投诉信,结果不了了之。
早在1990年,美国精神医学会就证实,性倾向改变的可能性几近于零。但在中国,针对同性恋的治疗却方兴未艾,矫正、收费,再矫正、再收费,同志、医生、咨询师、焦虑的父母,共同繁荣了这盘“隐形的生意”。
“厌恶疗法”
2012年秋天,一个女孩在微博上向北京同志中心求助,她的“女朋友”被自己的父母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。同志中心试图介入,但孩子无法反抗父母,最终失去了联系。
这之后,中心开始关注中国的同性恋治疗。但甫一开始就陷入困境,负责人说,他们找不到愿意讲述治疗经历的同志,虽然在同志中心,他们就知道至少有两个人接受过治疗。
“他们说,这是唯一不想提起的经历。”
对同性恋的治疗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。弗洛伊德曾研究用精神分析法将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。1920年,他尝试为一位女同性恋进行治疗,通过催眠和精神分析,重塑她对异性的观感。但后来,治疗不得不终止,当弗洛伊德发现她对接触男性如此厌恶。
之后四十年,各种治疗方法层出不穷,既有简单的冷水浴疗法,也有新兴的激素疗法,通过摄入雄性或雌性荷尔蒙,改变性向。脑叶切除手术,也成为一项并不惊悚的选择,出于人道主义,也有专家认为对男同性恋,最好的办法,是“教育性”的嫖妓。
在这些矫正方法中,最流行的是厌恶疗法。将同性性冲动和惩罚以及令人厌恶的东西结合起来,形成条件反射。医生会提供同性的裸体照片或者性爱视频,当出现性兴奋时,有两种常见的选择,一是进行电击,二是注射“阿扑吗啡”类的药物,后者会带来剧烈的头痛导致呕吐。
在美国,197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,40个同性恋“病人”经受了5天的电击治疗,平均每人总共接受了1050次电击。
北京同志中心找到了李言,他是吴振的朋友,曾接受过长达三个月的矫正治疗。如今,他成了一名坚定的反同性恋矫正者。
那是2011年,李言和男朋友的地下恋情被对方的父母所知,男朋友被押回老家相亲结婚,他无力挽留,整晚失眠。
在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,李言做了一个决定,他要比男朋友做得更绝,他不要再当同性恋了。
在深圳的一家心理治疗中心,治疗师声称,同性恋是一种心理疾病,已经有很多治愈的先例,只需要三个疗程就能治好,每个疗程3000块,一次付清还能打八折。
李言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,他将自己的所有积蓄拿出来,还向人借了钱,“我只是说我有病,要治”。
电极被粘在下体,冰凉得让人不安,还来不及不好意思,治疗师就让他观看男同的性爱视频,鼓励他放松,发挥想象。
然后,电击开始了。“那个疼啊。”回想起来,李言咬了咬牙。
机器是自动的,每当他出现性反应,就会产生电流,像一根针一样,从一点划遍全身。电流过后,他开始发抖,剧痛之后则是头晕,五六次后,他有些迷糊了,但治疗师鼓励他继续,否则他的病会一直这样子,他该想想被父母知道的后果。
治疗师说,如果实在受不了,他们有皮带,可以帮他固定在椅子上。
这样的电击一周一次,除了身体的疼痛,更多的是恐惧,李言控制不了自己,一种强烈的耻感攫住了他,这就像是一种惩罚,在和他开着下流的玩笑。
两个月后,他突然被一种更大的恐惧吞噬,要是治不好怎么办?在这之前,他从未想过这种可能,但突然间,这种可能性像一道闪电击碎了他,他没法改变自己。
后来,他质问治疗师为什么没有效果,对方坦白,还有治了一年都没好的呢,必须继续治疗,这是对自己负责,也是对父母负责。但李言已经拿不出一分钱了。
几年后,李言将这次失败的治疗告诉了吴振,这成了后者决定“卧底”的动力之一,在起诉状上,他们这么写道,同性恋不是病,不需要治疗,更不能被矫正。
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