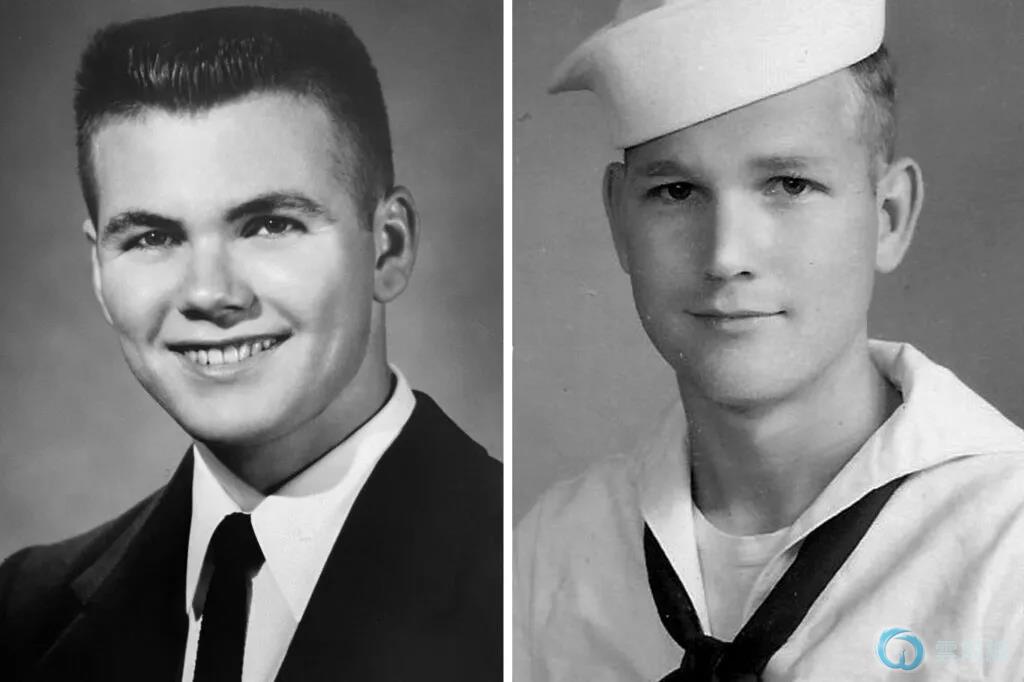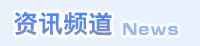 |
|

防艾大旗下的志愿小组
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,一夜之间,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
现实中则更为混乱。
政府的试水和观望,在2005年之后终于行动起来。一般的说法认为,中国在1997年取消了“流氓罪”,又于2001年将同性恋从“性变态”中剔除出去,这使得官方与民间社团之间有了合作的基础。
张北川回忆说,2005年11月,由中国疾控出面,召开香河会议。与会的各个省级疾控中心工作人员,带着各省的Gay参与会议。这种联席会议之前也召开过几次。
事实上,一个更大背景是,此时,各种用于艾滋病干预项目的国际基金进入了中国。
2002年,中英项目的启动,使得各地志愿者小组日益增多。而在2005年之后,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,一夜之间,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。这些志愿者小组全都汇聚在防控艾滋病这杆大旗之下。
“初步统计,中国目前应该有300多家志愿者小组,”张北川说,“全球基金到今年已经是第六轮了,盖茨基金也开始进入了中国,这些基金都是通过政府部门,比如各地疾控中心(CDC)以及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再分配到各个志愿者小组。”
CDC和志愿者小组之间,有着复杂而纠葛的关系。“CDC是通过志愿者小组来开展工作,有些是招募当地已经成立的志愿者组织,有的则是CDC自己成立了志愿者小组,”嘎嘎说,“比如天津,几年前,天津同性恋志愿者组织只有深蓝和另外一个同性恋者网站,到今年第六轮全球基金进入后,则一夜之间冒出了10多家。”
与张北川《朋友通信》项目组资助的志愿者小组不同,基金之下应运而生的小组,目标明确———采集各地CDC需要的数据。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,发放避孕套和动员MSM(男男性行为)人群前来抽血检测。检验结果可以显示艾滋病在某个区域的大体情况。
“操作方式很简单,只要你拉到一个人去抽血检验,被检验人可以得相应的报酬,而志愿者小组也可以得到其中提成。”爱白成都青年活动中心的负责人江华医生说,“这样做的后果变成在买卖一种标本,同一个人可以重复或者到不同检测点来抽血,重复采量得到的数据是不真实的,等于在造假。”
在过去的几年,成都爱白青年同性恋者活动中心几乎是唯一不参与MSM人群检测的组织,“没办法来保证咨询的质量,盲目推行的话,将是一个灾难。”江华说。
灾难的预兆在重庆已经发生。重庆彩虹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周生健向记者证实,2007年重庆MSM人群HIV感染者的检出率为14%,今年实际上还会更多,而成都也超过了10%.
在离开重庆时,一位正在读研究生的Gay(男同性恋者)拉着记者的手说,“拜托你一定要呼吁,已经很严重了,其实我是知道的,身边的朋友、同学也有人得那种病。”
“一般说来5%就已难以控制了,”张北川解释说,“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好些年了,这么多志愿者小组,事情也都在做,但形势却非常严峻。”
“告诉他们如何防治,更甚于抽血检验,”江华说,“检测前的咨询,往往被忽略了,而检测之后,只给一个结果,所有事情都完结了。”
在青岛,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关爱互助组织,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写给市长和卫生局长的一封控诉信:“青岛市CDC仅是在发现HIV感染后对感染者进行告知和感染因素调查,没有进行科学有效的心理疏导,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对感染者进行随访,未提供治疗知识和健康咨询,也不为感染者提供交流和分享治疗经验的平台。”
“CDC不可能像同性恋组织那样,为社区尽心做事,他们要的只是检测数据。而志愿者小组之间又狼牙交错,为了争夺资源,彼此倾轧,”北京市纪安德咨询中心主任郭雅琦说,“到现在,你可以看到,大多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,是在干一件事———拉人抽血,”
“纪安德”的前身正是“BP机同志热线”。2002年,创立热线的元老转向中国女同性恋运动,由于没有“艾滋病”这样招摇的旗号,中国的女同性恋运动,尚在艰难起步中。
但即便最苛刻的批评者(比如甄理)也承认,通过没完没了的会议、项目培训、考察交流,各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之间,往来频繁,而且意见趋向统一,“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。”
基金乱局
志愿者小组之间为了争夺资源,摩擦、指责、报复甚至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相互倾轧
中国同性恋社群浮出水面并走向组织化的过程,其动力也正是这些“乱源”。这次采访,恰逢《朋友通信》十周年。十年对于张北川来说,或许是满头青丝到银发的变化,但对于中国同性恋者们来说,从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,他们吸取到了养分、力量,并且茁壮成长。
另一股“乱源”来自万延海,这位年轻的医生,在早年干了件“极不光彩”的事———让公安局去抓捕同性恋者来配合研究,这使得他成名之后仍被人诟病。
但在此之后,他却“因从事同性恋运动”也被公安局短暂关押,他因此感到愤怒,并先后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,在那里看到了网络带来的神奇变化。
2005年,再次从美国回来的万延海带回了大量资金,他说,“基本上,今后做同性恋社群活动,自己不用挨饿了。”接下来又强调说,“国外各种基金会纷纷找上门来的。”
在张北川的叙述中,有了钱的“万医生”,工作作风发生了变化,扶持一派志愿者打倒另一派志愿者,他想控制社区,“举民主之旗,行独裁之事,”张北川说。
“这样的话无需辩驳,你只要看看,在这个人群当中,谁在实实在在做事,谁在夸夸其谈,”万延海反驳说,“我们发放的安全套是最多的,我们发放的心理学的读本、法律的读本是最多的。中国女同性恋的整个运动的发展,经济上的支持主要是我们。”
两位在90年代初结识的同性恋社群专家,聊到彼此,时常龃龉相向。
事实上,基金乱象是表,内在的原因在于各种基金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,以及缺乏真心真意为同性恋社群做事的人,甄理评价说。
2005年3月,香港智行基金会在内地开展工作三年后,张北川向联合国举报称,“智行基金会在开展艾滋干预工作中,存在志愿者小组间制造混乱,以及财务不透明等恶劣行为。”
这使得基金乱象开始公开化。不久,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了《关于张北川举报智行基金会的调查结果》,否认举报信上的指责。但一位内部人员告诉记者,此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也很慎重在中国开展项目,“至少与智行基金之间的合作明显减少。”
类似的指责信,智行基金会在2007年9月也写过一份。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在给西安同康工作组安然的信中,指责后者对于志愿者小组间的摩擦、山头主义(抢占地盘)以及其他恶性竞争的问题。
安然回复说,实际上是智行基金会利用提供工作经费,许诺配备笔记本电脑,将同康工作组的一名负责人挖走,采取不正当竞争方式,试图分裂和瓦解同康工作组。
志愿者小组之间为了争夺资源,摩擦、指责、报复甚至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相互倾轧。“而进入这个领域的资金都各怀心事,它对社区发展不发展根本不在乎,有些人就是拿着钱组织一些人培训,完了之后就不管了。”甄理说,他挺怀念“在之前那个年代做同性恋社群工作的人,有公益心,也很单纯。”
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