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|
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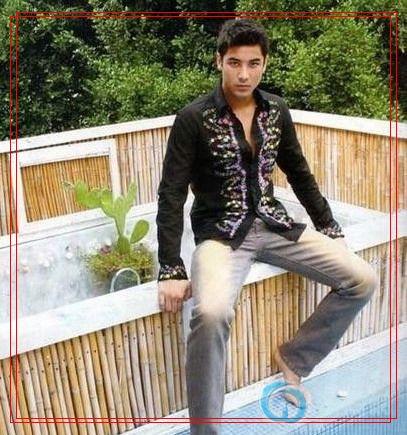
小雨和着风时缓时急地打落在玻璃窗上,一滴,二滴,三点……最终聚集成一条条,弯弯窄窄的小溪,沥沥流下,就像情人脸颊上的眼泪97的最后几天是在医院里度过的,每天躺在病床呆呆地看窗外,天气阴霾,雨雪交替,爸和妈也交替守护在我身边,白天和黑夜
98年的春节对我来说是最灰色的,我几乎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回忆着跟他一起生活的一幕一幕。我拼命地抽着香烟,烟雾缭绕,火红的烟头飞舞着,然后我把它落向自己的左手腕上,一次又一次。我没有子虐倾向,可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来缓解来自内心的疼
于是,过了春节快开学的时候,我又病倒了,一病就是一个多月。又见桃花的时候,堂姐从北京回来了,说要跟一个北京人结婚。我无法理解,只能轻叹世事无常。堂姐90年考上北京大学,跟她一起考上的还有和她念省常中的男同学,后来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她看到我的样子十分担心,说我不宜再整天窝在家里,邀我去北京散散心,起初我不想去,后来她说你总要去喝我喜酒吧?我拗不过她,我是独子,我们自幼感情很好,我一直把她当亲姐姐的
儿时爷爷奶奶带我去过次北京,不过记忆已模糊。爷爷是老新四军,他和奶奶是解放北平时认识的。那天来接站的是我未来的堂姐夫,初见他时,我就被这个器宇轩昂的男人吸引住了。他大概三十二,三岁,180标准的北方个儿。帅气的平头,浓眉大眼,微挺得鼻梁下留着精心修饰过的两撇胡须。一身笔挺的西装更是衬托出那副伟岸的身材,一切显的成熟,精干。他打开一辆‘凌志’的车门,我跟堂姐钻进了车。一路上我心里已释然心想,堂姐,你真行。
初见杰是在堂姐的婚宴上,那天宾客都到齐了,就我旁边的一个位置一直空着。到了过了开席时间十几分钟,才看见一个魁梧的男人匆匆赶来。当时我诧异地看了看做在我身边的这个男人,又看了看对面的堂姐夫,怀疑这是这是一场电影的特技镜头。他们两长的太像了。等到敬酒时堂姐夫称他哥,我才释然。这个男人确实比堂姐夫多了份内敛和威严在眉宇间。席间,由于我们经常敬酒。有时起身落座会碰到对方,弄的没喝多少酒的我一阵阵头晕目眩。有一次我夹了块菜,刚往嘴里送,那该死的正好起身碰到了我的右胳膊。于是那块菜在我身上滚了几滚,落在我的大腿上。nnd,当时给溴的555,好在大家喝了酒,脸上大都是红红的。这时他也察觉自己闯了祸,赶紧取了张巾纸递到我的面前。我在接过巾纸时意外发现,那是双保养很好的手,雪白的衬衣袖口下掩不住一撮乌黑的汗毛,一直延伸到小指。十指修长而有力,要命的是连每个指关节上还有汗毛。晕……‘对不起啊,’我在低头擦拭污物时听到一个磁性的男中音。我抬头发觉他在看着我,眼里却没有一丁点的歉意,倒有几分挪揄。我不由气结,小声道,‘您醉了’。‘哈哈,这点酒算什么?等会儿我还得开车送你们回家呢。’男中音回敬。
喜宴散后,杰负责送我们几个常州亲戚去豹房“堂姐租的房子”,新房在亚运村。我被安排在副驾驶室坐下,一路上,我晕晕地盯着那双性感而有力的双手在不停地飞翻,无耻地竟把自己想象成是那双手下的方向盘。
|
|











